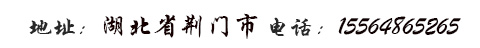家传小港李家的百年繁华上
|
宁波镇海小港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小镇面对烟波浩森的杭州湾,背靠四季如茵的宁绍平原。入镇口,一座挺拔青翠的小山——江家山耸立在路旁。转身远眺,地平线上的四明山影仍隐约可见,甬江静静地环流而来。这得天独厚的佳境,在风水先生眼里可是块宝地。 据老辈人说,尚在秦始皇年代,这里就有渔贩盐贾的贸易。唐明皇时,当地的张、崔、李几大姓就东渡日本去做生意。其后宋、元、明、清几朝,这里的下海人或藐视禁令,或劈波斩浪,负起了敢为天下先的使命。被称之为“近代中国实业缩影”的小港李氏家族,正是从这海隅小镇闯进大上海的…… 宁波镇海李氏家族纪念馆 赤手闯上海:李也亭沙船起家 李家在小港本非大户。李也亭9岁丧父。年(清道光二年),他15岁只身到上海南码头曹德大糟坊当学徒。家中寡母叶氏和长兄弼安靠几亩薄田度日。弟兄俩以承字排,他名承久,兄名承辅。按糟坊规矩,学徒任务之一是给客户送货。那时糟坊门前江滩上停着一排排大沙船,船工们个个都是好酒量,自然那是李也亭每天挑酒必去的地方。所谓沙船,长十丈余,宽二丈,深一丈五六,平底高桅,巨橹广舱,一船可载货百余吨。在洋轮未来之前,它是中国海运的主力。当时上海已是沿海贸易的中转港,“帆墙林立,舶舶蔽江”,新来乍到的李也亭不禁目瞪口呆。 春来秋去,他很快和船工们混熟了。船上老大见他人小机敏,便怂恿他:“小阿弟,可敢和我们去下海?”李也亭挠挠头,烧酒营生固然奔头不大,可一纸学徒契约却不是说废就废的。船上管上货的耆民(经理)过来搭讪了:“你若肯来,我去讨个情。”果然,凭这一句话,糟坊老板碍着老客户的面子,竟放了人。李也亭便到郁森盛船号当了船工。这年,他19岁。 当时,船行规矩允许,每船上货,伙友可捎一些私货以补薪资过低。虽说进货好孬及销路畅堵全凭个人眼光,不过,每趟下来多少总能赚些钱。自然,船东肯让出这份利,为的是海上若遇风险大伙能同生共死。李也亭天生是一块经商的料,他货既进的俏,交际也蛮有一套。当年由南运北多是米糖纱布,取货要现银,他哪有这么多钱?幸亏他结识了钱庄跑街、同乡人赵立诚,他唤赵是“大阿哥”,赵喊他为“小老弟”。李遵母训,为人信义第一。一笔帐讲好啥个日脚清,必提前一日送到。赵很乐意为他筹款。这样几年下来,他竟攒了一笔钱。一天,他乐呵呵地去找赵立诚:“大阿哥,我想自己弄条船。”赵吓了一跳,问:“你可晓得置条船要上万两银子?”可听了李也亭九九归一的一本细帐,赵不禁手拍大腿说:“好!我帮你一把,就看你命中有无财运了。”那时沿江造船商很多,只要付一半定银,保你三个月船就下水。沙船出海向来结队而行,主要是防海盗袭扰。于是,他就加入了老城厢郁家、慈溪董家的北号船队。当然谁也不曾料到,就靠这条船,李家竟后来居上,成了上海滩风流百余载的工商巨子。 李也亭(-)浮雕像 说到创业,李也亭确是费了不少心血。一般船东都把船交给老大和耆民去管,他却趟趟随行,甚至年近半百时还是如此。大约是老沙船正值目光返照,朝廷也新将潜运由河运改为海运,继而中英鸦片媾兵、太平天国起事,兵连祸接,沙船承运的南北漕粮有如水火之急。时任天津漕运局总办的张友堂也是宁波人,李也亭持乡晚辈名帖求见,自然受到不少照应。因而仅仅几年功夫,他不仅开办了久大沙船号,从一只船发展到了10余艘船,还在十六铺上游处买下一块滩地辟为久大码头。 十六铺码头的大沙船和小沙船(从左至右) 久大沙船号筹办甫定,李也亭马上又盘算起新的生意来。和赵立诚的交往,使他深知钱庄也是一个很有讲究的行当。它开设资本虽不大,那时老城厢最叫得响的钱庄也只不过万把两银子,但关键是股东必须富有资产,能偿付得起。放贷只要对象牢靠,吸进存款运用得当,赚钱是自然的。何况,“久大”每年两季航运进贷,都是向别家钱庄贷银两,如果日后改向自家钱庄贷,岂不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吗?加上“久大”沙船已独立成队,还有一些散户船跟着走,拉它们向李家钱庄贷款,更是顺理成章之事。于是,他和赵立诚商定,用经营沙船的利润合开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不过,钱庄一切营业仍由赵主持,对外不声张李家也投人巨资。因为,当时储户最忌讳钱庄放款给沙船,因航运毕竟风险太大,一只有闪失,储户自然是本利全蚀。赵立诚是经营钱庄的一把好手,他有多年跑街结下的客户,又熟知老城厢里各种行当的底细,于是,这三家钱庄一开张就红火起来。 李也亭在上海发财了,但脑子里还是有老框框。他总认为置房买地是积攒财产的最好方式。于是,他一面将久大码头相邻的油车、竹巷两码头及周围地皮买下,一面又往乡下捎了几万两银子,让长兄弼安买了余亩田租人耕种。同时,在镇上盖了一处气派颇大的宅院。宅第分东西两院。东院由弼安居住,称为乾房;西院称坤房,由他和妻儿居住。自此,宁波小港李氏家族便分为乾、坤两房。家中一切均由弼安执掌,听命于老太太叶太夫人。无庸讳言,老兄弟俩当年对跻身官宦门第的欲望都很强。李也亭同许多红顶商人一样,在同治初年花了两银子捐了个国学生花翎盐运使、同江苏候补知府的头衔。 李也亭60岁那年,正在寿庆日子,他的沙船队却在海上遭遇数十年未遇的飓风.大半沙船倾覆了。这对他恰如晴天霹雳。一并罹难的郁森盛号沙船队则更惨,据说共有数十条船被大海吞没。当年还没有电报,消息是在风暴中死里逃生的余船到港后再用快马传回来的。李也亭闻讯眼前一黑,顿时瘫倒,从此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家人和管事齐集榻前,他关照将所遗产业一分为二,钱庄中“崇余”归乾房,“慎余”归坤房,“立余”为两房共有。当弼安问及沙船号事,他手指大侄儿听涛,吩咐众人:“日后凡属行中事,全归听涛调度。”众人愕然。因久大沙船号是李氏产业总管理机构,三家钱庄都听命于它,这等于是把全部家业都交给听涛管理。李也亭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断断续续地说:“不论子侄,只以能者为劳……”听涛闻言,上不住泪如雨下。 年,辛劳了一生的李也亭去世了。他的灵柩还未发回故土,久大船队的余船却奇迹般地回来了。因那年到达北口的船很少,所载去的货销得极畅,价亦卖得俏。同样,北口码头因船来的少,货亦积得多,进价自然廉。返回上海又是货稀价高,这一来二去,损失倒也没有预计的那么惨重。可惜李也亭什么都不晓得了。 至于他的传奇般的发迹史,上海的李氏后人所知也模模糊糊了。闲聊起来,还掺杂着沪上宁波巨商叶家(澄衷)、张家(梓林)几乎雷同的传说,都是巧遇贵人、拾到重金、如数璧还、后被提携等等。当笔者告知以上历史梗概,他们似乎还有几分疑惑。及至说明40年前李也亭曾孙祖韩曾给有关部门留下一份访问笔录可以为证,他们才“喔”了一声。不过,笔者所交谈过的李氏后人都尊称也亭为“发财太公”,这倒是众口一词的。 任凭风浪起:李听涛稳守家业 说到李也亭立下的家训,不能不提及乃兄弼安。老兄弟俩可谓手足情深。弼安虽始终未曾离乡,而对家族贡献也不小。宁波开化很早,但传统道德观念却特别深。弼安不愿离开,除忠厚寡言外,还有便是孔老夫子的古训:“父母在,不远游。”他身为长子,侍奉寡母是他职责。叶太夫人年轻守寡,独立抚养两子长大,晚年高寿,安享天伦之乐。李也亭虽多次返乡省亲及回家奔丧,而平日里嘘寒问暖、侍奉汤药,均是老大操劳。其母于年(清咸丰七年)89岁去世。老哥俩把父母合葬在小港临海的江家山顶,建墓庐鹤麓山庄,可说独占了当地的风水之胜,以至李家后人对家族发达有一说法:“是两位曾祖太公把高祖太公、太婆的茔地选得好,所以后人得发了。” 小港李家家谱简表 李弼安在乡中对子侄教育管束颇费心思。他请县里名塾师朱老夫子来开蒙授课。他的三个儿子听涛(名高源)、濂水(名高濂)、雨田(名高沛),也亭的独子梅塘(名高嘉),都在家塾一道读书。后来他的次子濂水由县考秀才而省试中举,继于光绪二年丙子恩科会试以三甲一百六十五名荣登进士金榜,至今北京孔庙的进士题名榜上还有濂水的姓名、籍贯。有趣的是那块碑上李高濂的“高”字磨损了,以至有些书上称他为“李濂”。他自醉心科举就从不再过问家中商务,高中后仅留京做了个户部主事的闲京官。不过,在旧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浓厚风气里,他毕竟给祖宗父辈脸上添了莫大光彩。小港李家府前竖起了高高的旗杆,船刚进港就能看见。而濂水此时步入仕途,恰逢神州大地面临列强宰割。各类新潮勃兴之时。虽为京中闲官,但国势的艰危、朝政的窳败、志士的蝶血,这一幕幕他都亲见了。作为一个正直的读书人,他忧时伤世,子侄们和他或通函或交谈,分明能感受到那一份深深的爱国之心。这或许就为日后众多李氏子孙投人辛亥风云和抗日烽火播下了种子。 弼安对兄弟援手最力的是“久大”刚亮出牌号时,他就把16岁的儿子听涛送往上海,协助叔叔经营产业。老兄弟俩那时便商定,日后凡李家子孙都须进人自家商号学徒三年,然后方可享用家族供给。听涛照这个规矩,从船上水手干起,吃苦耐劳,虚心求教,几年间将行中事务初步摸熟。也亭晚年体衰多病不再随船,便由听涛在码头调度一切。他处事周到谨慎,深为叔父满意。也亭去世前二三年,英国旗昌等洋轮已横行南北洋和内河航线,国中朝野呼吁要自办商轮。北洋大臣李鸿章曾召人密议,打算由官府一举收买沙船暂作缓冲,因当时沙船业已面临重重危机。传至李也亭耳中,他心头自有一番思量。环顾家中子侄,梅塘是他独子,但自幼体弱,不曾经过乘风踏浪生涯;濂水是求功名之人;雨田从未离乡;只有听涛能在此天旋地转之机担起这份重任。 十六铺码头停泊的洋轮 李听涛接手家业,叔父重托自是不敢疏怠。他审时度势,深谙沙船业已如强弩之末,只有果断收缩方为上策。然而,退出的资金又该投放何处?冥思苦想之中,他想起一句俗语:“船儿离不开港。”不论是洋轮或是土轮,都必须靠港,这就少不了码头。因此,他第一步先把久大等码头修整扩建,并造起两层楼新式栈房,除供自家沙船所用外,还供别家船只和华商火轮停靠。在加强码头经营同时,听涛又致力于扩展钱庄。李家钱庄原本就近开在南市,租界日益繁盛之后,设在租界内的北市钱庄逐步兴旺,不论资金和户头都超出了老城厢。听涛便和家人商议,除将“立余”仍留南市外,“崇余”、“慎余”都迁往北市的江西路宁波路口,聘钱业才俊郑郎斋、袁联清等分任各庄经理,还正式加人了北市钱业会馆,成为汇划钱庄。所谓汇划钱庄,是老钱庄为适应时代发展,引进新式金融单据制度改良而成的。它由公会统一印制公单,只须手续齐备,各庄不得拒收。而汇划钱庄又必须是资本厚、信誉佳的行庄,它的一般资本银虽仅五六万,而实际周转资金都须百万以上。由于上海发展处处需资金调剂,若经营得法,钱庄获利甚为丰厚。大钱庄平均获利每年达30万两以上。年北市钱业会馆购地16亩,集资12万两,在闸北塘沽路建造新馆舍。李家钱庄摊银一万两。新会馆门楼、檐廊、厅堂无不雕梁画栋,成为沪上一大景观。 正与也亭、听涛叔侄的预见相符,沙船在数年间果真是一落千丈。这更使李听涛下定决心将资金重点移往钱庄。 时值列强外资蜂拥侵人中华,海外冒险家和各色骗子在金融界掀起阵阵恶浪。如年的丝业囤积倒闭就是一例。先是金素记丝栈亏折银数十万两,牵扯钱庄40余家歇业。上海道告示严禁“闭歇潜逃”。谁料这才刚开头,紧跟着胡雪岩阜康银号也因囤丝太多而陷人绝境。随即上海钱庄便同雪融冰化一般,接二连三地倒了十之六七,街谈巷议几乎“谈钱色变”。险情如此,李氏家人岂不心惊肉跳!好在李听涛心眼“死”,年前丝行红得令人垂涎时,曾有人劝他投资。他却认准:“我家靠沙船生意,沙船做的是米糖豆麦,钱庄放的也是这宗款子。丝行是湖州钱庄做的,我们不去抢。"赖此一念,他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 谁料事隔数年,上海又刮起一股贴票风潮。这是潮帮钱庄兴起来的。它为争夺游资,耍起了一套贴票把戏。即凡以90元存入者,开一年期票,届时可兑一百元,年获利息十之一。这在当时实属惊人,前去存款者踏破门槛。一些老钱庄坐不住了,也有人劝“慎余”、“崇余”试一试。李听涛断然表示:“不可。”果然,年冬天,一场金融风暴骤然而起。那些贴票钱庄因无法如期兑现,被储户轧坍柜台,于是,全上海为之震动。当时《申报》连篇累牍地报道风潮始末,起始曾把“慎余”对人停闭庄中,后又作更正,称为访事误录。这真可谓有惊无险。李听涛在清末实业机遇和风险并存之机,能艰难守业,这为家族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石。 开创房地产:李詠裳才识过人 李听涛生于年(清道光14年),满60岁后他就在考虑交接班之事。李家此时已成为一个大家族。乾房这边他本支号孟房,有一独子昌祥名厚益。老二濂水号仲房,有七子六女。七子以长幼排为耘清、詠裳、瀛翔、翼之、善祥、康祥、寿祥,名厚培、厚垣、厚埏、厚堉、厚坊、厚埰、厚圻。女儿因还袭封建陋规,只知嫁给谁家,大名连她们的孙辈都不知晓了。老三雨四号季房,也只有一子叫北平,名厚璇。坤房那边堂弟梅塘虽为独子,但他却是多产,有七子三女,仅比进士公少养三千金。七子为云书、玉麟、如山、薇庄、征五、鸿祥。屑清,名厚祐、厚祉、厚祺、厚礽、厚禧、厚祯、厚祚。三千金分别取名金娥。银娥、玉娥。这两大房子侄加起来共有16人,倒让李听涛为选中一人而颇费踌躇。而上辈“不论子侄只以能者为劳”的祖训又不可违背。于是他也决定传侄不传子,将大权交给濂水的次子詠裳。 李氏子侄从那一辈起,基本都不在乡间居住,多数在上海、北京读书进学。虽读的仍是四书五经,而西方的声光电化,民约人权等也渐耳濡目染。詠裳自幼随父长在京城,眼界见识更是开阔。17岁回上海在家中钱庄学生意,循规蹈矩,没有丝毫纨绔习气,深为老经理们所赞许。后又随伯父结识了不少商界名流。30岁上,李听涛便将久大沙船号经理一职委托给他。实际此时的沙船号,真能撑住场面的倒是码头。久大码头这时分外兴旺。大达、宁虞等公司商轮均租此落脚,后来虞洽卿办宁绍公司也借用过久大码头。李詠裳便以码头为基业,组织了镇康新记公司,在油车码头附近的祖地上建造了吉祥弄。这是李家投资房地产之始,也是上海最早的石库门房子。二层楼砖结构,厚墙壁,小窗洞,窄长的天井,厅堂厢房还维持旧式乡居程式。李詠裳住弄内2号,公司也设在那里。 李詠裳接手后,又逢一次良机。年前后,江浙绅商受美国虐杀我侨胞事件的刺激,兴起一股“实业救国”浪潮,不少人甚至变卖家产建厂修路。钱庄可以调剂资金,自然成为热门产业。李詠裳便和众兄弟相商,以总号名义再开一家会余钱庄。坤房那边的众兄弟也一个个按捺不住了。于是,先由老七屑清从本房慎余支款在年前开办了同余钱庄。紧接着,老三如山也仿效再开了崙余钱庄。可以说,李氏连续新开了三家钱庄,很大程度上依仗了家族在上海已立足70年的势力。詠裳这一辈的姐妹兄弟很多都嫁娶沪上名门望族。梅塘的长女金娥嫁给了濂水门生、中过进士点了翰林的夏启瑜。次女银娥嫁给了柏墅方家二房的方选青。长子云书又和上海酱业大王张鼎新园主逸云分别娶郑氏钱庄的大、小二位小姐,结为襟兄弟。四子薇庄又娶方选青的妹妹为妻。这还仅是坤房部分儿女的婚姻情况。这种亲套亲的关系无疑对李家事业是一大助力。即以新钱庄开张之日来说,有交情的老钱庄都要去存上一笔款子为贺礼以厚资金,俗称“堆花银子”。方、郑几家都开有钱庄,尤其方家是宁波帮钱庄首户,拥有安康、瑞康、汇康等20余家。李氏三家新钱庄开张,虽说资本银都为两万,但哪一家“堆花银子”不收到十多万至数十万两的? 宁波人在上海开的钱庄老照片 李詠裳的眼光、魄力确实比他的上辈又高一筹。他在投资钱庄同时,又将重心移住房地产。当时租界中心地带南京路一段已如繁花似锦。他和坤房兄弟商议,认定下一个热点必定是偏西的静安寺四周地段。于是,由“久大”出面组织了天丰、地丰、元丰、黄丰四大地产公司,取中国古语天、地、玄(元)、黄之意先买下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北一块50余亩地为天丰所有,次又将徐愚斋遗业柿子园亩地买断为地丰公司,再东移至杨树浦路平凉路置地建元丰公司,最后又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小沙渡路(今西康路)、西摩路(今陕西北路)、新闸路、武定路一圈购地60余亩,成立黄丰公司。这着棋使李家在顺应时势上占尽了风头。不消几年,这些地块不论是售地还是建房租售,都在原价上翻了一番甚至几番。尤为世人瞩目的是,当时公共租界工部局要在柿子园和新闸路两地块筑路,竟无理地无偿征用李家土地。租界本是外国人强加给中国的耻辱,它还要如此蛮横地剥夺华人利益,李氏家族据理抗争,最后工部局只得同意李家自筑马路。于是,在租界内便有了以国人公司和堂号命名的马路。李家将北起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南至徐家汇路(今华山路)穿过柿子园的这一段马路,定名为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随即又在新闸路相近的槟榔路(今安远路)至劳勃生路(今长寿路)间自筑了李诵清堂路(今陕西北路)。李诵清堂即为李氏坤房堂号。马路筑毕,尽管租界当局百般挑剔,但也不得不承认路基、路面都达到了规定标准。马路开通,贺客盈门,这大长了国人志气。自然,马路两侧的房地产身价也攀高直上。李家坤房一支以后便长期聚居在这里。 今日上海陕西北路一角 李詠裳对奖掖后进也不遗余力。谈起他的往事,现仍健在的李氏80岁上下的老人都能道及一二。比如,当年房地产之战打响后,李氏钱庄便逐步收场了。因此到解放时,除“同余”一家尚存外,其它五家都为历史陈迹了。实际上就是“同余”,真正股本也不为屑清子女所有了,只是拥有人借用老字号而已。但李詠裳却在花甲之年还和人合开恒巽钱庄,其动因只为看中他的表侄俞佐庭是个金融干才。俞佐庭19岁进“慎余”当学徒,一直当到钱庄和银行经理,直至宁波商会会长。这年他重返上海想干一番事业,詠裳亲自出马张罗,请他当恒巽庄经理。俞果然不负表叔厚望,不仅钱庄办得好,商界也有人望,不几年当上了上海总商会执委主任。更令人感佩的是,在子侄们成长起来以后,李詠裳便悄然隐退了。年他逾83岁高龄才溘然长逝,是同辈兄弟中享年最高的。 投资拓荒业,李云书堪称先驱 假如说李詠裳是把主要精力用在家族的实业发展上的话,那么他的兄弟、尤其是坤房的几位堂兄弟则已远远不满足于此了。大约因李梅塘喜爱读书结交文人,府中郑观应等人的《易言》、《救时揭要》等书刊任凭子弟传阅。甲午次年,李濂水从京城护送母亲灵柩回籍,路经上海与兄弟子侄见面。其时正值《马关条约》新签,他讲起朝中西太后专权,权贵们一味忍辱求和,翁同稣虽力争却势孤力单。说着说着,他竟忍不住黯然泣下。这时,那些年轻子侄都不禁怒形于色。不久,南通状元张謇弃官南下高擎实业救国大旗,李家兄弟都成了他的拥护者。其中要数梅塘长子云书最为活跃了。 论年纪,云书不仅在坤房,即使包括乾房,他在兄弟排行中也是老大。故而当时商界人士中称云书为“李家阿大”。他是也亭公生前亲手抱过的嫡长孙,在家中的地位自是举足轻重。听涛未选这位大侄儿管理家业,倒不是因为他不能干。云书16岁便进慎余钱庄做学徒,写算记帐样样拿得,只是他和乃父一样喜欢结交文人雅士,颇有些“海派”。当时年纪相仿的王一亭在他家钱庄学生意,因心思多在学画上,柜上师傅屡加责难,这位少东家却多方庇护。风声传到听涛耳里,他很不放心。偌大的家业交给云书这样管,岂不坏事?好在詠裳对这位大阿哥倒十分尊重,凡事将就着他,所以云书是最早从家中钱庄宕款投资别项事业的。 李云书最初投资的企业是天一垦务公司,这是宁波另一巨商严信厚发起的。当时国人目睹日、俄觊觎东北,吁请清廷开放荒地移民以固边唾。清政府同意在锦州一带招垦,每亩地价仅为银一二分。李、严集资80余万两雇人拓垦,然后熟地以每亩银一两余出售,获利十分丰厚。由于此举旗开得胜,他的投资欲望便愈发旺盛。他先后投资了上海绢丝、永裕垦业、大达轮步等十数家公司,还独自募股修建了杭州从江干到湖墅一段铁路。因此云书博得了“投资大王”的雅号,有关他投资的故事也流传得又多又奇。比如他和虞洽卿等人合作投资四明银行,最初发行的四明银行钞票无人肯接受,他便让李家钱庄代为发行。钱庄自然要承担较大风险,他却满不在乎。又如,李家参股大达轮步公司后,久大码头即为大过专用,不得停靠外公司商轮。虞洽卿办三北轮船公司,码头没有着落,先找公司总办刘锦藻商量,被拒后转寻协办李云书谈,李一口答应了。因码头原为李家产业,刘也只得听其作主。此外,他提携外甥方液仙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一事也有口皆碑。方液仙的父亲原不赞同儿子办日用化学品厂,为此家中闹得不可开交。他母亲只得拿出元私房钱来帮儿子,娘舅李云书便也拿出1元人股。不料后来经营大有起色,方液仙要扩大投资,打算再请叔叔方季扬人股。方季扬对李云书投资这么“滥”不放心,偏要李退出他才人股。李云书二话不说立即照办。由于李云书为人豪爽,所以他在商界人望很高。年上海商务总会改选,他继曾少卿后当选为第三任总理。同时,他还兼任了上海交通银行总办、清农工商部议员等职,俨然成了上海商界头面人物。 孙中山等在李家门前合影 这时的江浙绅商其实均已不甘心事事听命于清廷。张謇首先发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云书和四弟薇庄同为会员,他还被选为会董。当时大约李家坤房的经营中心都已迁人租界,所以在会员表上住所一栏都填“二洋径桥北大余号”。那里即是今天的延安东路四川路口,历经百年沧桑,现已无法辨寻当年遗迹了。预备立宪公会吁请清廷实行新政,实际也就是利用皇权来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为此发动了三次轰动朝野的签名大请愿,腐朽的清政府不予理睬。这就导致许多人在失望中转向了革命党。李氏兄弟即为其中活跃分子。据说介绍云书加人同盟会的是他年轻时的知交王一亭。王一亭辛亥革命前夕担任同盟会在上海的筹饷负责人,到处为起义军筹款。他鼓动说:“云书兄,眼下已是千钧一发之机,我辈商界男儿岂能作壁上观?”李云书不禁为之动容。李家兄弟大多倾向革命,于是便推他阿大出头张罗。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时,云书还出任了兵站总监,而实际管事的是他的五弟征五。笔者曾见到一份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密电;“联军总兵站已分派李厚禧(即征五)。陶逊充副总监。”所以此后的催械电都称:“陈英土都督、李征五总监。”这曾让很多人不解:他弟兄俩到底谁是总监?李云书又干什么去了?近日笔者见到几份当年的文件,方解开心头之谜。原来在联军起兵之时,负筹款总责任的中华银行亦一并成立。它初以黄兴为总董,孙中山回国后改孙为总董,李云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为董事。其行址就设在李家南市久大码头。不仅如此,连沈缦云的沪军都督财政长事务所也设在那里。这样一来,李云书怎么还能分身过去?在他那里,不仅代发过最早的中华民国公债票、军用钞,还代收过各界助饷捐款。因为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请詠裳在吉祥弄镇康新记公司代设了中华银行经理发行处。可惜这段史实因辛亥之后纷乱不己而被长期湮没了。 就在国家陷于新的动荡时,李云书的投资事业也遭受了重大挫折。民国初年曾刮起一股强劲的大办实业风。孙中山要修20万里铁路,黄兴组织了拓殖协会,连章太炎也挂上了东三省筹边使的头衔。李云书心头更热。他自以为有清末在锦州垦荒发财的经验,于是,竟把巨资投向了遥远的黑龙江边唾黑河、呼玛地区,在那里组织了一家三大垦牧公司,围垦荒地,种植小麦,再建厂制成面粉,然后顺黑龙江漂流而下到海参成,再转海轮运到天津、上海出售。这种魄力真可谓中国现代边疆拓荒的先驱。然而毕竟路程太远,运费太昂,旧中国黑势力之猖撅更使他防不胜防。他派留日学农的次子祖圣去当垦牧公司经理,而随兄长一同去游玩的九子祖耼却被当地“红胡子”绑走,索票价几十万元。消息传到上海,全家乱成一团。经人讨价还价,最后还是坏掉了一大笔钱。这一不幸事件将他的投资热情彻底扑灭了。边垦事业草草收场,欠下的债务据说是将新闸路老宅一幢白洋房(即今上海大学商学院)变卖后才偿清。年李云书在上海去世,享年68岁。 “借款”官钱局:李薇庄含冤早逝 就在李云书为革命奔波时,他的兄弟老四薇庄、老五征五也投身革命洪流,并在那场大波澜中各有一段“秘史”。 薇庄本是读书进学之人,由举人而放官做过候补知府、江苏糖捐总办。清朝末年,各省督抚纷纷设官钱局发行纸币敛财。正好这时,薇庄升任了江苏裕苏官钱局总办。而官钱局的病商害民,使他内心极为痛苦。一则他本钱庄世家出身,切身利害有其一份;二则清廷腐朽早使他积愤在胸,只碍于头上的顶子不便发泄。 年,他奉命到日本考察银行,住在东京佐佐木寓舍里。门房通报有客来访。延见之下,不料竟是老世交赵立诚的儿子家艺。原先李、赵两家合开钱庄,李也亭去世后,赵家便在苏州等地另设庄号。家艺自幼在城内吴大徵府中读书,后娶了吴的侄女、吴湖帆的姑母为妻。但他和兄长家蕃都是一不愿做官。二不肯经商,在日本留学时竟迷上了孙中山的学说,加入了同盟会。之后他便走南闯北,不是为起义筹款,就是联络各路人马。他听说薇庄到了日本,专程前来密访。那时节,这些已沐欧风美雨的商家子弟,对清王朝的认识早趋向一致,只看是否狠得下心来投身一搏。经家艺一番鼓吹,薇庄便颔首应允。于是,李薇庄在起身赴日时,还是大清四品命官,回国之际却已是革命党人了。 武昌一声炮响,党人群起响应。陈其美急欲在上海下手,苦的是没有经费。他先找来虞洽卿、李征五等人,由征五出面,让老六屑清的同余钱庄作保,暂从宁波同乡会借到了湖州水灾捐款元。但这点钱顶什么用?陈其美双手一摊,那几位便都面面相觑。征五问:“你看要多少数?”陈其美报出需购枪械子弹等一长串数字,说着双手一比划,起码要先搞到10万元。这让众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征五沉思片刻,心想:“除了官钱局,谁能搬出这么多银元?看来只有动四哥的脑筋了。”于是,便和虞洽卿、孙泉标等人一同去寻薇庄。薇庄早料到有这么一天。但这大宗款项眼下即便有,也已有了用途,即供江南制造局造枪械用。要想取出来,还须该局总办张萍初署印。他们密议后又一起去找张葆初,一说是薇庄设计诱张就范,一说是征五等人软硬兼施。总之,这笔钱是拿到了,由虞洽卿交给了李平书,成了上海起事的第一笔大宗经费。当初议定由附和起事的宁、绍、杭、湖等埠商号同出借据以为捐饷,待事定后归还官库。不料事隔几日,便有人向江苏巡抚程德全密告,说官钱局有人舞弊,程派人来查,果然空空如也。薇庄亦无法道出真相,因而被拘押于苏州知府衙署。可叹经战火涂炭,起义虽告成功,原议定认捐还款的商号却多因亏耗或歇业而无力偿付,于是有人对这笔钱的去向恶意中伤。薇庄一怒之下,便把借据全部焚毁,以示独力承担。在缧泄之中,他曾满怀忧愤作《秋夜感怀》诗二首,书于一柄纸扇之上。尽管陈其美、于右任等党国要人都明白他的冤屈,民国元年同盟会总部上海机关部改选时,他仍当选为评议员,然而这种百口莫辩的中伤对他的精神摧残太大,不久便于民国二年去世了,年仅41岁。 孙中山赠李薇庄题词 李薇庄死后,长子祖韩、次子祖夔将他写在扇面上的《秋夜感怀双定诗》装裱成册,请当年战友和名流题诗作画以为纪念。先后题诗作画者有于右任、李平书、王一亭、沈曾植、袁克文等30余人。现存的尚有任重专为他辛亥被囚一事所作的《吴门谪居图》,以及林琴南为他毁据之举所画的《焚券图》等。其中,蔡元培的题诗最能道出此中真相:“家藏遗墨在,一发耀秋晖。朗抱见风月,幽怀想蕨薇。人间多可恨,尘世复何依。忍忆谪居处,龙孙几度肥?”蔡又题款日:“辛亥岁季,薇庄先生因事中于小人之谗谪羁苏州府署……”孙中山先生了解此事后,也亲笔题赠“子孙永保”四字。可惜薇庄原诗和部分书画题作,都在“文革”中散佚了。最令人痛心的是,抄家风匝地而起时,薇庄的三女秋君竟亲手将中山先生题词的上、下款剪掉了。笔者见此残存遗墨,深为长叹不已。 (本文转“北仑新闻网”,原文连载于《上海滩》年,第7、8、9期,作者不详,在此向原发网站及作者致敬,转发未经许可,若有异议请告知我们,即刻删除。) (图片来自视频截图)版式编辑∣宁海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angshouhuaa.com/cshjz/8385.html
- 上一篇文章: 种植心中的绿色,我们共同抗疫情西韩小学少
- 下一篇文章: 5种公认好养的花,颜值还不输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