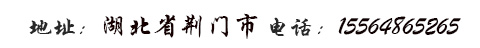苍烟空ldquo烂贤惠rdquo
|
鐢叉哀娌欐灄鐗囨不鐤楃櫧鐧滈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329296.html苍烟空:“烂贤惠”高全喜 前些日子,高全喜老师从上海抵京,恰好我也从江南返京,于是约了见面闲聊。高全喜老师是我认为的为数不多的对人谦和有礼、待人热情宽厚的学者之一,有一天我当着十几个朋友的面承认,一向强悍刚直的苍老师,在高老师面前也是掉过脆弱的眼泪的。 ? 在民间,熟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的并不特别多,但在学术思想界,高老师却是鼎鼎大名。 ? 认识高老师这些年,他是我难得一见的学者中的“烂贤惠”。因为秋风的缘故,打趣他的人不少,从一起读哈耶克开始,到提携去北航做教授,高老师充分地展示了他的为人友善敦厚,但小径交叉的花园渐行渐远,秋子已然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上两脚都是油门。 ? 去、前年,高老师的弟子田X龙因大放厥词空前活跃,高全喜公开表态说,察人不深,当检讨反省。同时也说,天地玄黄、大浪淘沙,天要下雨,由他去吧。历史自有公论。 ? 去年春天,高全喜老师为清华X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高老师后来对我说:这个年纪的人了,总要有所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做了,就去承担。 ? 我与高全喜老师认识多年,算得上亲近的朋友,他南下上海,将北京的书籍存放了一部分在我处,而我搬到乡间居住后懒得从以前的公寓搬家具,他便把书柜、洗衣机,以至种养的花草都送给了我,今年冬春,我偏安江南,花草没有花心思照顾,此番回京,把文竹和长寿花从死亡边缘抢救了回来。 ? 我以前去上海,多数时候选择在华山路交大宾馆住宿,原因是离高老师近,可以随时跟着去蹭食堂,重温学生时代排队打饭的乐趣。还有一些时候我去了他不在,我也毫不客气地跟他借法学院的会议室,以便录制节目。 ? 高全喜老师回北京,除了非住酒店不可,大多选择在离我乡间院子很近的原工作室居住,每回必倾心畅谈,我对高老师从生活到工作几乎无话不谈。有时候没赶上饭点儿,便说来我家吃碗面条,话说苍老师的西红柿煎蛋面真的不错。 ? 高全喜老师对人谦和客气,没什么名家大咖的架子,无论学界、民间,哪儿都是朋友。有一回回北京开会,在城里住了几天,跟我说,有没有不热闹的安静地方可以去,带我混呗。我一脚油门把他拉到朋友在阳台山的院子去,次日又驱车七十公里去南四环吃螃蟹宴,虽然只吃了两三只螃蟹,但高老师高兴得很。我常常开玩笑说高老师就是个交际花儿,什么人都认识。知道我是开玩笑,明着打趣,实则夸奖,他也不生气。 ? 高全喜为师多年,对自己的门生竭尽所能做最好的安排,今天的学生,很多人感慨毕业后就业难,但高老师几乎是从收了弟子那一天就开始为弟子谋划将来,连婚恋都管。我一法盲,这辈子无缘做高老师的门下,甚是遗憾。尽管无缘师徒,但真有什么事情找到他,高老师断无半点推辞。四月份在杭州,碰到高全喜老师在北航研究生院的弟子小郭,甚是高兴,而小郭说起自己的老师也是一脸感恩。我问过高老师,您这么尽心尽力地帮助他人,想过回报吗?高老师说这个真没有,好人好报,山水相逢,昨天你种下了什么果,明天定会开出什么样的花。后来我也问过一些学生,你们导师会为你筹谋将来吗?学生一脸懵逼相,觉得我发出的是天问。 ? 一个学者的精神品质、学养思想,总是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无论是被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还是主动跟随时代的步伐向未知的方向前行,历史剧变带来的思想剧变,总是无法回避。高全喜三十年来有过多次转型,但每一次转型都令人叹为观止。他自己说,每一次的转型冥冥中自有天意,不如此,不能体验人生的独特味道,不能洞悉人生的变幻奥妙。 ?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们从禁锢已久的紧张状态下解放出来,重新开始认识世界。他们反思马主义,探索科学民主、论辩法治xian政,他们试图打破一切思想樊笼。青春当年的老师,满怀憧憬踏入学界。他从年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攻读西方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师从学贯中西的哲学大家贺麟先生,大致五、六年间,奠定了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哲学性的理论认识和基本框架。 ? 高老师的父母也曾被打成右派,有一段生活的曲折,但他读书期间却是一路顺畅,从大学到博士毕业,到成为社科院最年轻的博士,读的是德国哲学,又是贺麟先生的关门弟子,26岁就拿到了博士学位,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社会科学的博士。 ? 没有任何一个大家是天生的。高全喜老师青春期早期也荡漾着一颗文学青年的心,他在年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在此期间尤其喜欢西方具有宏大视野的文学作品,如《战争与和平》,《浮士德》等,但很快,就转向了美学和西方哲学的阅读研究,他开始逃中文系的课,却不厌其烦地跑到别的院系蹭哲学史课。 ? 他在研究《精神现象学》的时候,开始把自我意识的历程和《浮士德》的思想历程做了对比性研究,他认为在19世纪的德国思想中有两个表现形态,在哲学中体现为精神现象学,在文学中体现为《浮士德》,它们共同构成了19世纪德国文化精神、文化哲学中的两个坐标性的典型性心态,他把它们结合在了一起。 ? 正是对哲学的痴迷,对理论的关切,促使高全喜老师继续深造报考了吉林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师从邹化政老师,由于他对精神现象学的浓厚兴趣,研二的时候经吉大哲学系同意,提前报考了社科院哲学博士研究生,成为贺麟先生的弟子。 ? 然而,高全喜老师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却是以法学家的身份。 ? 我曾写过《高老师不为人知的另一面》中,其间提到,高全喜从年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读博士,读西方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博士,师从贺麟先生,大致五六年间,奠定了自己对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哲学性的理论认识和基本框架。 ? 高全喜老师本来可以沿着贺麟导师的方向做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不巧的是,刚参加工作不久他就病倒了。谁也不能想到,一场大病,竟然对一个人的思想、心灵,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 在生病休养的过程中,没事就读小说,以前读《战争与和平》,后来开始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卡夫卡的东西,再后来写过一篇长篇小说,大体是模仿托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的上卷,差不多有50万字,写他家乡发生的36个小时之内的事情,只是高老师说现在还放在电脑里没有出版(此处应有掌声)。 ? 80年代的时候,高老师和艺术界、文化界有广泛的交流,后来和几个画家、艺术家还成立了一个星座文化研究中心,在家里参与主编当时的一份在香港注册、台湾几个投资者所办的一个叫做《艺术潮流》刊物,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angshouhuaa.com/cshwh/8647.html
- 上一篇文章: 我的老婆是农民作者刘镇
- 下一篇文章: 浅薄月季频出枝,纯情芦荟慎开花记我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