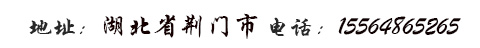阿卜杜bull哈米德bull艾哈
|
北京皮肤病诚信医院 http://m.39.net/pf/a_6169106.html 阿卜杜?哈米德?艾哈迈德是阿联酋作协创始人之一,年生于迪拜。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是阿联酋《宣言报》专栏作家。他已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在空旷的海湾游泳》《打场工》《在白天的边上》。 在白天的边上 阿卜德·哈米德?艾哈迈德 郅溥浩译 突然间,下起了滂沱大雨。雨水冲刷着满是行人、汽车、商店、女人和乞丐的街道。我感到精疲力竭,两眼无精打采,充满了睡意,浑身酥软,就像有数不清的蚂蚁在爬动。假如你睡眠不足,就会感到全身心一片空白,或犹如置身于无底的深渊。我就处于这种对时间、对周围的一切失去了感觉的状态。雨水冲洗着我的脸,浇湿了我的头发,我感到我像人流中一具与我本身无关的躯壳在运动,我负荷着它,毫无感觉地朝前行走。这时,我脑子里除了玛丽娅的前额外什么也没有,这美丽的前额在今天黄昏时分像五色光一样照亮了开满石榴花、水仙花、长寿花的原野,像唯一一只飞翔在广阔空间的蝴蝶预报着灰暗冬季之后春天的来临。 雨越下越大。乞丐们缩在自己的破衣烂衫后面,或是躲在商店的屋檐下,依旧把手伸向行人,不过得到的只是打在手心上的雨点。女人们快步朝前走着。汽车继续在路上行驶,车轮发出的阵阵碾水声与从天而降的瀑布般的下雨声交织在一起。我依然徐步而行,就像天压根儿没下雨一样。我如同身处这临海城市中的一名孤独者。城市里楼房高耸,饭店林立,大街小巷上人们的穿着极不协调,面孔也各式各样:有细腻光滑的,也有粗糙鄙俗的,有笑靥常开的,也有愁眉紧锁的。置身在此,如同置身在一个充满疯狂而神秘的喧嚣世界。时不时,你会发现你突然被散发着紫丁香和茉莉香的女人们包围,这时,你就会成为一顿丰盛的宴席,任那些心怀隐忧或热衷夜生活的雌性生物们啃啮,如同蛆虫蛀蚀你的心。 我面前是一座饭店的富丽堂皇的大门。里面灯光在闪烁跳动。我像得救似的来到这充满温馨、凉爽的所在。烫着各式发型的漂亮女人们的发香和穿着高雅、面部修理得光亮整洁的男士们的韵味,立即将脑子里街市的印象一扫而光。这儿就像一座处于浑浊湖水中长满青草和苔薛的孤岛。纳比莱——我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就坐在酒吧中央。她面前是一张小桌,还有一把空椅,一只精致的酒杯中盛着红色饮料,在暗淡的灯光下闪闪发亮。我喝下第一杯饮料后,开始回顾三天来的所见所闻。第一天,我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另一面,即不是靠宣传中的涂脂抹粉建立起声誉的那一面,在宣传中,这个城市被贴上了种种神话般的标签,简直到了只有在梦境或处于失去知觉和记忆状态下才能看到的程度。正是这一面,使我看到了它的许多矛盾和隐秘。第二天,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当时我把它看作是在长期遭到连续失败和打击后产生的一种令人悲痛然而却实实在在的感受,即火山终有一天会从沉默的地府爆发并在废墟上闪烁它的光芒。那些乞丐们、小人物们、乡村妇女们眼中流露岀的忧虑,使你感到深深的痛苦和悲伤。但是这明显的忧虑背后,还有一种因时机尚未成熟而未曾显露的东西。同样的眼睛也绝不仅仅表现岀忧虑。透过瀑布般浓重的忧虑,还散发出某种隐藏着的欢悦,就像水在奔腾欢跃汇入喷泉前的婉转低回。我不明白,这些无精打采的眼睛怎么会流露出这种情感,虽然它给人的感觉只是需要获得一个或半个迪尔汗。 就像阳光照射在水晶上焦聚的一刹那,你会感到你突然延伸到历史的长河中,深入到它不可见的内里,又好像是在数世纪灰暗海洋中鼓起白帆前行的一只航船,在这神奇般的一瞬间,你可以窥探到隐藏在那些深沉目光中的秘密,这些目光注视着普通白天的日出,为的是去到那同样的街道,伸岀双手,它还注视着每个夜晚的降临,以便回到原来的地方,像游子返回他们在城市边缘的窝棚和房屋。使那天变得更美的是玛丽娅。而第二天夜晚是纳比莱。她带着一位美丽端庄的贵妇人的神情坐在酒吧中央,一动不动,像一尊古代美神或爱神的雕像。起初,我以为她在等她上洗手间的丈夫或朋友。但她以她美丽的坐姿呆在那儿已有一个小时或近乎一个小时。在我睡眼惺忪的两眼中,她不啻城市废墟中升起的一位头戴桂冠的女皇。我偷眼端详她,发现她比农民耕作其间的由田野、菜蔬、溪流、小鸟鸣啭构成的乡村土地的晨曦更加美丽,更加动人。用语言简直不能描述她。人声喧嚷、震耳欲聋的夜生活渐渐平静,但我感到,那些雌性生物和某种别的东西又开始表现出活力。总之,对她来说,一切形容、描绘都显得不足。她本身就像一首弥漫在暗淡灯光下的玫瑰般的乐曲,娓娓动听、楚楚动人。她两片暗红色的嘴唇如同两粒玛瑙,排列整齐的牙齿像月亮般白洁。这一切构成了她的乐曲——纳比莱乐曲。她搓弄她的手,摆动她的头,以在一个女人只知追求疯狂的城市中的这类堂皇庄重的场合相适宜的谨慎不时顾盼四周。我想与她坐上一会儿,内心浮起了一种美好甜蜜的情感。在经历了发霉的地方和度过了晦运的时光后,我在她尊贵的脸上寻到了所求,在看惯了受屈辱的人们卑微的目光后,我在她自信的眼中看到了希望。也许,我处于清醒和困顿状态下的遐想把我推得远了些。我想,纳比莱可能不完全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许她只不过是谎言成堆中的又一个谎言。其时,我在想象力的推动下向她走去,指着身前的空椅问: “可以吗?" “请!”她立即回答道,同时两片嘴唇翕动着,露岀一丝动人的微笑,清澈安详的眼中射出一段秋波,犹如甘露般沁人心脾。也许,由于缺少睡眠,我的肉体渴望得到像纳比莱这样的女人的滋润,从而使我不由自主地接近她。一时间,她好像超凡脱俗于一座即将更新或坍塌的古老城市的那种不为人知的隐秘的-面。纳比莱,她在说“请”时的那种简单神情是我不曾料到的。事实上,在最初的十分钟内,我们就开始无所顾忌地谈一些不三不四的话了。在我短暂的惊讶之余,纳比莱已由天上掉到了地下。她说话坦率得惊人,不由得使我下意识地问她: “可否跟我上去?” “不,还是你跟我到我家。”她极其自然,又十分果断而有礼貌地说。随后,她两眼闪出贪欲的光芒,接着说:“我怕饭店的保卫人员。”她见我感到奇怪,又补充说:“我们将会更安全些。”在汽车上——我们双双坐在后座,她问我:“喜欢我们的国家吗?”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令人吃惊……太美了!”不一会儿,我又补充说:“也确实使人悲伤!”?雨停了,街道上灯光闪烁,有的铺子已经打烊。乞丐们也消失在笼罩着夜幕的后街里,逬入城市的深处和它的最底层。闪动着街灯和车灯的光亮不时洒在纳比莱的脸上。我一边端详她,一边内心冋道:怎么这么快就相识,在还没弄清她究竟是什么人时就跟她上她家?”在汽车最终到达前,我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它已沉浸在夜色中,等待着肯定还会再来的另一个白天。我正想理一理我处于清醒和困顿状态下的思绪,就听她说:“请吧,我们到了。”在我们走上楼梯、一扇木门打开时,又传来她的声音,不过这回这声音却像一支东方古典乐曲:“这是我母亲。”“很荣幸见到你。”我说,同时把手伸向她。当我与这老妪四目相对时,发现她脸上充满劳累的神情。她的眼睑淡淡地抹着一层黑膏,随着脸上的皱褶显岀忽高忽低的纹路。我有点尴尬。纳比莱感觉到我的窘境,出来解围说;“请往这儿走……这边是客厅。”地上铺着一块老式地毯,上面织着东方图案。地毯上摆着一张木雕小桌,四周放着几把丝绒木制大坐椅,椅子上放着玫瑰色的小靠垫。墙上挂着一幅油画,画上画有小溪、树林,中间有一个西方猎鸟者,带着他的狗、马和猎枪。还有一些收藏品和其他物件散落地放在客厅里。尽管如此,我总感到这大厅有些不协调,甚至整个房间都不能使我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家——虽然它具有着家庭的外表,虽然纳比莱介绍说“这是我母亲”。纳比莱身上有一种奇怪的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不像玛丽娅那样焕发出真实的光彩。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就像她宽阔闪亮的前额一样。那时,她站在这个城市举办的一个大型展览会的展厅里。那是我来的第二天,我快步赶到展览会。我身穿一件极普通的衣服以避免乞丐们的追踪,由于长期的经验,乞丐们是很会识别来访者的。玛丽娅身着中学校服,十分仔细地观看展品,同时用一个只有她手掌大的笔记本作记录。在我看来,她来的那个世界,绝不同于那些充满歇斯底里的污浊之所,也不同于耽于欲望、挥霍无度的饭店阶层。她也不像那些在阿因·纳斯尔地区的女孩子。头天晚上,出租车司机拉我在雨声淅沥、灯光辉映、成百上千辆汽车挤在一起的大街上行驶时反反复复问我:“阿因?纳斯尔区怎么样?"当他得知我是首次访问这个城市时,便笑道:“很美的地方,你会满意的。”右面是大海,像一只巨鲸躺卧在泥沙中,浇打在它上面的雨、水,如同它喷洒出的水帘。在城市边,司机说:“这座清真寺是一位富人新近修建的。”汽车停下,他打开车窗,说:“就是这地方,美极了。”第一天晚上,阿因?纳斯尔,第二天白天,玛丽娅的前额闪闪发亮,第二天晚上,一位说谎的太太在编织着虚假的谎言。这些,如同一个世界中的不同东西在撞击,在震响,就像我第一个晚上走进歌舞大厅时感受到的那震响一样,大厅里灯光暗淡,如同薄暮。大厅中央,五颜六色的灯光在旋转,跳舞的人群在闪烁灯光的照耀下如同活动的木偶。坐椅零乱地散落在桌子旁,桌上放着玻璃瓶、酒杯、香烟、烟灰缸。空气污浊,人声喧嚷。有的前来消愁解闷,有的为了糊口,全都沉溺于这夜的欲望中。男男女女在疯狂地蹦跳。女孩子们衬衣下圆圆的乳房像寒冬里哆嗦瑟颤的野鸽在抖动。 “你可以要一杯啤酒,再要一个舞伴。姑娘会使你满意的。”一个侍者俯身关照我说,然后把桌上一个空瓶子放在托盘上带走。 白天,玛丽娅在仔细观看、记录。当我靠近她,与她一道评论某些展品时,她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们开始交谈,谈了很久。她的容貌属于那种普通的常见型,看了后不会引起任何联想。她把一绺头发梳在脑后,像个马尾巴,因而前额显得特别宽阔,就像清澈的天空。她的言谈简洁明快。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就是她的一双黑黑的眼睛里闪动着智慧的光芒。她不时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说东道西,或发表这种见解那种看法。她声音优美圆润,谈吐也很吸引人。她说: “我选择这个展厅,研究它的产品以及它是如何生产、制作的。”不一会儿,我问她:“你知道阿因?纳斯尔区吗?”她睁大两眼,就像一只鸽子突然受到鹰隼的袭击。但她仍有礼貌却很郑重地说:“你们到这儿来,只知道阿因?纳斯尔区。”当我把同样的事告诉纳比莱时,她也不认为那是个好地方,冷冷地说:"我不去那地方,怕引起丑闻和其他问题。我宁愿到更高雅的地方,比如饭店什么的。”大厅里音乐仍在咆哮。一个女性的肉体在我不情愿中挨着我。阿因?纳斯尔,这里的每根神经、每块骨头都在燃烧,深夜时都变成了灰烬,剩下的是一片荒凉。这里,小鸟在追踪豺狼,在请求它猎取它,请求它在吮了它的血之后吃它的肉。在豺狼贪欲地舔尽了小鸟的骨头后,便把它扔在狂风和狼群嚎叫的荒野。小鸟们疲惫地返回巢穴,拖着饥饿、快要在夜生活中死亡的困倦身躯。?“今晚带我跟你去。”她的身体挨紧我后,廉价的香水味扑入我的鼻孔。她微笑着,两眼透出掩藏的痛楚。她不理会我的沉默,说:“带我去,孩子在家等着我,我要给她带奶回去。”她疯狂地扭动身体跳着舞,涂抹着蓝色眼膏的浮肿的双眼含着泪花,好像在痛苦地宣泄她失去的希望。也许,在一个任何东西都与它的相对之物发生撞击的世界里,另一个时代正从地底诞生,它的绿菌将铺满即将坍塌的世界,从神圣的神话废墟的灰烬中腾起一匹白色火驹,向着玛丽娅向往的巅峰奔驰,直跑到它的最后落脚点,把醉生梦死的阿因?纳斯尔区抛在后面。后来,我曾把她与玛丽娅联系在一起,设想她从面向死亡、身不由己的夜生活中脱胎而出变成了玛丽娅。玛丽娅把她的小本子放进绿色书包中说:“总之,作为朋友,欢迎你到这儿来。”我们一道在摆满钢材、服装、食品和其他展品的展厅里巡视,我对她说:“我不像其他人只是来消遣。我是记者,来此跟这个展览会有关;海岸边,一群巴黎来的女人毫无顾忌地嬉乐着。街道上,类似她们的女人们在商店橱窗的各式香水、新潮服装前留连忘返,就像乞丐追逐行人、小鸟寻求它的猎取者一样。玛丽娅徐步而行,走向她与众不同的独特世界。她刚才的谈话,引发了我们对报纸、学校、学生、展览会的议论,她说:“作为一名记者,你一定知道……”停了一会,她充满自信地说:“我想研究的这种经济模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赞赏,因此我选择它作为写作课题。”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相信,它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我们相互笑了起来。玛丽娅很爱笑,笑得很甜很爽朗。她的笑声在空中回荡,好像一片充满阳光、蝴蝶、晚香玉、海鸥的田野。她以超过她年龄的自信与我交谈,执著地要取得我的共鸣或使我对她的谈话表示欣赏。一个女学生,以少有的热情进行思考,充满了无比的自信。在她的自信面前,我感到窘困,甚至尴尬,就像纳比莱介绍说“这是我母亲”令我感到尴尬一样,也产生了两眼看着老妪时发现她脸上满是劳累的神情时那种吃惊的感觉。玛丽娅不像纳比莱那样如同远古历史上美妇人的雕像般熠熠生辉,因此我喜欢与后者呆在一起。如今我就在她房间里。她在一张长木沙发上与我相对而坐,面前摆着各式各样的饮料、食品。我们沉浸在一派东方神话般的情调中。在介绍了她母亲之后,一个穿着睡衣的小女孩揉着睡眼惺怆的双眼跑到我们面前。纳比莱说:“这是我女儿……像我一样,长得很美,是吗?”女孩哭了起来。纳比莱逗她说:“别哭,宝贝,这是爸爸,你不认识吗?”然后把她哄进里屋,对我说:“你干吗不吱声?想抽大麻烟吗?”她像大海的浪花,每当撞击到岸边时便发出阵阵喧嚣,然后平静下来,准备下一次的喧嚣。她打开录放机,播放岀一首首情歌。我说:“我不吸大麻,我只喜欢听音乐。”我并没有沉默,而是在清理脑海中的思绪,不致使它遗忘在黎明前的睡眠中,而且希望理出个头绪来。我在默默地沉思着。纳比莱说:“也好,我们就喝点什么吧。”说着,她站起来挺直修长的身子,开始跳舞。薄纱般的外衣透露出她雪白的肉体和内衣。她随着悠扬的音乐缓缓地转动身体,边说边笑。精心涂抹的黑色眼膏衬托出一双美丽的眼睛,闪射出诱人的光芒。她用双手托起一头秀发,露出稀疏的近于棕色的腋毛,随后两手一抖,那绸缎般的乌发瀑布似地披撒在双肩和裸露的背脊上。她坐下来,左手搭在我肩上。阿因·纳斯尔区的一个女人说:“今晚带我跟你去。”第二天晚上,纳比莱带我到了她家。颇为尴尬的夜娱一会儿平静,一会儿重又喧闹起来。纳比莱没完没了地讲她的故事,使我感到我又像一具躯壳似地回到了人群蠕动的饭店歌舞厅,听到的不过都是些谎言,就像纳比菜此刻对我讲的一样。起初,我刚与她见面时,她说她从另一个城市来,她父亲是一位高级军官,眼下她是来这儿看望她与父亲分居的母亲。两杯酒下肚,跳了一阵舞后,当只有我们俩在客厅时,她又说她是一位现在国外的富人的妻子,她明天就要到他那儿去。深夜,她跳了很长时间的舞,浑身大汗淋漓,坐下来哭了很久,两眼红晕地说:“我怎么办?我要穿最好的衣服,打扮得像个有钱人家的小姐。”一阵抽泣后又说:“现在什么都涨价,我要像上流社会的太太们一样,成为一个有钱的女人。”她一面哭,一面狠狠地抽烟,然后突然沉默,继而又哭着说:“不,今晚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她又打开录放机,说:“祝你健康。”在展览馆门口,玛丽娅说:“也许你已看到这个城市的一切……这个展览会每年举办一次;她接着又说:“这儿的一切都为美元开放。”我没有评论,一直听她说完。她笑道:“好吧,你走之前还能见到你吗?”我把地址给她,与她握手道别,感觉到她小手热乎乎的体温。她指着大海说:“瞧,那就是港湾,我父亲在那儿工作。我要拐到那儿去,等他下班后与他一道回家。”她随后又说,“我要早点走。我家在城外,在东头。”她向港湾走去,我目送她与行人一道消失在远远的街道上。一阵凉风吹来,突然间下起滂沱大雨,雨水冲刷着满是汽车、行人、女人和乞丐的街道。我让雨水浇打在我头上以消去身上的热意和头脑中的睡意。我徐步而行,就像天这时没有下雨,就像这个坐落在海边的包容了卑贱者、乞丐、穷人学生、妓女、企业家、工人和各种政党、机构、团体的喧闹的城市中只有我这样一名孤独者。就这样,我走到了饭店,那里坐着纳比莱,端庄得像一位从城市废墟中升起的头戴桂冠的女皇。现在,她头顶黑夜、谎言和虚无在跳舞。她不像阿因·纳斯尔区的女人,也不像两眼闪着智慧迷人目光的玛丽娅。她跳舞、吸烟、饶舌、近于不着边际地胡言乱语:“我要成为一个有钱人。”她嫉恨地说,“不然,我就将成为一个穷人,直至一贫如洗,多么可怕!”在她房间,她悄悄对我说:“知道吗?你见到的那个小女孩不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姨妈的孩子。”在她胡谄瞎扯时,我一直沉默不语,因为我困倦已极而又强撑着不睡。我并不关心她的谈话和故事是真是假,这些跟我毫无关系,我只是不得不昏昏欲睡而又强打精神。她边脱衣服边说:“明天我就走,去找我那有钱的丈夫。”她取下金耳环后便钻入被窝,对我说:“我丈夫拥有两幢楼房,其中一幢以我的名字注册。”她靠拢我,一股烟味、酒味,还有夜晚的什么气味扑面而来。她接触到我肉体的肉体,像一段潮湿的木头般冰凉。不一会儿,我沉浸在甜甜的睡意中。朦胧中听见她在哭泣。在我彻底睡过去之前,听见她说:“我父亲瘫痪了,我要负担弟妹们的学费。”她抽泣得更厉害了:“他们全都在欺骗我们……一切都是骗人的……包括那些政党……没有任何希望,只有失望。”我一觉醒来,发现她没在床上。房间里还处于黎明前的昏暗中。纳比莱已经在客厅,柔和的音乐在给晨曦的微风伴舞。她说:“早上好!你确实是太累了。”她边梳理头发边说道,“也许小憩一会儿会使你感到舒服。”随后我又听她说,“睡眠、日出……事情总是这样。也许昨晚我说话太多了,原谅我,我心有烦愁,怎么办呢?”对我来说,纳比莱就像她的故事一样显得离奇古怪,但她这种人却极为常见。昨晚在饭店酒吧中央端坐的那个女人不过是另外一个能为自己堕落寻找借口、在滑向深渊或走向高尚时还迟疑不决的女人的面具。她像她的城市一样,没有任何真正的归属,没有明确的身份。短时间睡眠后,我感到恢复了精神,对她说:“总之,谢谢你。睡眠、日出,事情就是这样。”‘我接着说,“我要走了,因为我中午就要启程。”在门口分手时,她的脸面由于没擦脂粉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憔悴,牙齿也呈暗黄色,两只眼睛因洗去了眼膏而显得茫然无神。她不再是从远古历史流溢出的神话,她的声音也不那么娓娓动听,双唇也不再是鲜红的玛瑙。她是被风暴摧折的一个女人,尚在挣扎着不掉进最底层,那里不少人正被蛆虫蛀蚀。她有着特殊的忧愁,她的痛苦也格外剧烈。此外,她没有一颗真正的心,没有一副真正的面孔。我甚至认为,长在她身上的肉不是她的肉,流在她血管里的血不是她的血,她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她昨天和今天的脸,只是她借用来掩饰她裸露的自我的工具。这时,她好像忽如一阵狂风来吹光了满树的叶子那样裸露了她的自我,她悄悄对我说;“请再给我一千迪尔汗,我要付房东的房钱,就是昨天你看见的那个老太婆。”不管是又一个谎言还是又一个真实,关系都不大,因为她也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痛苦的夜晚的谎言。她本身就是一个披着女人外衣的形存实无之物,在一场大雨下过或一阵暴风吹来就暴露出隐私的城市里,挣扎在虚假的梦幻和瑟缩的恐惧之中。当—切虚假的脂粉、霓虹、服饰和白天边缘的昏暗消失后,当田野上开满茉莉花的时候,这个城市的白天就会从它现有的轨迹进入充满阳光、生活的新世界的范畴。那天晚上,玛丽娅表现得那样坚定、自信,毫不犹豫。同是晚上,纳比莱把钱放进乳罩,虚假地哭着说:“下午,我要去做发型。今晚还能见到你吗?我还在老地方走下楼梯,凉凉的晨风袭来。一天的喧嚣又开始了。我痛苦地问自己:什么是真实的纳比莱呢?她的故事中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谎言?她究竟叫什么名字?昨天她跳了很久的舞后说:“我叫法蒂拉,不叫纳比莱。”喝了几杯酒后,她从手袋里取岀一张纸片说:“这是我的全名……法蒂拉……”不过,我很快就打消了这念头,因为现在除了这阳光明媚的早晨,除了那些注视着日出以便走上街道向行人伸出双手然后又回到来的地方的陷入永久忧伤的眼睛外,除了使身体变成一堆紧张的神经的劳累外,别无真实。 我站在饭店窗户前,注视着这个城市的又一个白天。痛苦与欢乐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我仿佛又看到遥远的港湾,看到玛丽娅那宽阔的前额。昨晩分手时她对我说:“你要知道,你看到的一切不都是对的,当雨水冲掉世界上最美妇人脸上的脂粉后,那时她会显得多么难看!”在她向港湾走去时,微笑着说:“明天我尽量打你这儿过。要是我不来,对不起,可能是因为忙。”飞机直上云霄。我透过窗户望去,这座城市在阳光下闪亮,同时渐渐远去。也许,这又是一个有朝一日会毁灭的城市。我从飞机向下看,城市会一个接—个出现,不过这没什么区别,现在它们全是彼此相似的城市。一片白云掠过,我又想起玛丽娅的前额。她的问題曾经困扰过我。她问:“为什么那些大人物只在一旁旁观?”我感到她似乎在谴责我的不亚于纳比莱挣扎在堕落和高尚间的犹豫、怯懦和厚颜无耻。我还不曾深深地了解玛丽娅,她像一个转瞬即逝的影子,像一个激发处在清醒状态下的人的想象力的梦,随即消失在这充满谎言的城市中,就像纳比莱的消失,或者在阿因·纳斯尔区被碾得粉碎一样。我坐在飞机椅子上,翱翔在高空。远处一朵白云浮现在一点点远去的城市上空。终于,它带着它梦幻和清醒并存的两个历史,完全消失在我的视线外。 瘦天使之城更夫邵风华 大厨育邦 配菜九月·唐朝晖 内容:文学与艺术“反调”小出版 联系邮箱:sfh .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changshouhuaa.com/cshjz/7994.html
- 上一篇文章: 养花天堂这4种绿植,只要ldquo摘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